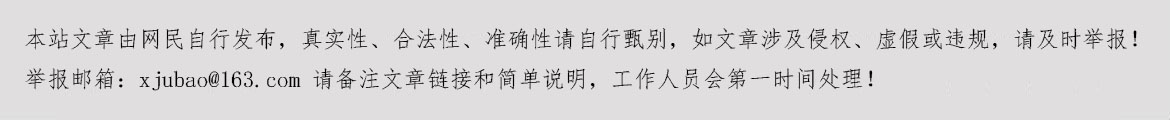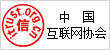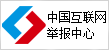我的大姨:女儿被拐,连生四娃被夫家阉割,失去生育能力
2022-02-05 20:31:00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全景故事】栏目独家约稿,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作者:冬生
大姨的名字叫吴春芬,今年68岁,大姨和许许多多的农村的妇女一样勤劳和善良,按部就班的过着她的咸淡生活。一直以为大姨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养养花种种草,后来直到某一次妈妈给我讲述大姨的故事,我才了解到,真实人生往往比想象来得更荒谬无常。
大姨的大女儿离家出走被拐,被蹂躏地不能生育;大儿子背井离乡成家立业,壮年离世,留下一个智力残疾的儿子;大姨夫找被拐女儿郁郁而亡,最后大姨改嫁一个暴躁的前夫,遭尽家暴。
1
我的大姨是1953年生人,她的母亲是一个裹了脚童养媳,11岁嫁给了大她8、9岁的父亲。因为西南偏远农村的重男轻女,作为家里最大的女孩,她的大哥能在该求学的时候读到高中,而她就作为家里最有力的帮手和劳动力围着炉灶,忙着田间,带着一个又一个接连出生的弟妹。
作为大姐的她从未上过一天学,是货真价实的文盲,60几年里认识的字仅仅是自己的名字,不会乘车不会取钱不会用智能手机,但我想或许未出嫁的日子才是她悲苦交加的一生中难得能休憩片刻的无忧时光。
20岁的大姨和许许多多农村妇女一般,和乡邻介绍父母认可的男孩结婚了。我大姨告诉我她结婚只有一个喜盆拿着这个盆子从一个偏远的山头走了6.7个小时,翻进了更加贫瘠和泥泞的山头。
大姨生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儿子叫大平,女儿叫大红。大红在15.6岁的时候,和声称自己打工经验丰富的17.8岁同龄的同村女孩前往大都市追求梦想,没想到这却是一生梦魇的开始。
一个来月,同村的两个务工女孩回家了,但大红却不见身影。大姨和姨父接连几天前往两个女孩家里从逼问到苦苦哀求就想知道大红去了哪儿,怎么不回来过年。十几天女孩们闭紧了嘴。只有在姨父问的气晕过去的时候支支吾吾的说了一句:被卖了,卖给了广元山里的一个鳏夫。只有山的名字,没有买家卖家的名字,15岁的大红就这样消失在生活中。
30几年前位于云贵川的偏远山村的大姨和姨父,在得知消息的隔天腿着就往镇上赶,为了搭上一天只有一趟的去往广元去寻找大红。凌晨3点走上5、6小时坐上去县里的大巴,辗转前往广元。一路艰难自不必说,不识字一辈子没出过山的农民夫妇,靠着家里人手写的字条问路问人,时令正值初夏睡在买个馒头就是一天,累了就睡在路边的草丛里。
最终打听到了一家农户,家中男人39岁未娶妻,好吃懒做靠着亲戚邻居借钱买了新妇。至此后的半月,大姨和姨夫日蹲夜守妄图能得知女儿大红的下落,可家里就只有传闻娶了妻的老头和一个老太太。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大红在离门口几步之遥的猪圈门后,仅能容纳一个成人蜷缩着猫腰躲着。大红像狗一样,或许还不如狗,被绳子拴着,几日的毒打和挨饿已经神经失语发不出一点声音。
日日耗夜夜熬,在不断的争执和对峙下,大姨和姨夫得以进屋寻人,可这个时候,大红已经被转移到了山里,蓬头垢面不似人形也就是这一次搜寻结果让大姨心灰意冷回家了。姨夫在回家后,心彻底伤了,身体彻底垮了,短短半个月就因生病撒手人寰。
大约又过了5.6年,大姨收到大红辗转拖来的口信得知现在她已经成了家生下拐子家的娃娃。在那个时候的农村,在哪家生了小孩,你就是哪家的女人了,不问你的来路也不问你的意愿,就这样生米煮成熟饭,生死都得由人了。后红的亲哥也远走福建,做了一个伐木工人。至此,这个家就真的四散奔离了。
2
图片来源于电影《盲山》剧照
在大红被拐的20年间里,大姨也另作他妇并在40岁时生下小女儿取名小慧。在落后封闭贫穷愚昧的乡下村庄,新姨父暴力殴打过婚嫂显得理所应当,或许大姨没有再期盼生活会变好。
某次,大红辗转回到了大姨的新家,她能回家省亲是因为买她的人家不怕她跑了,她失去了那个年代农村妇女的流动性-生育力。
母女就隔着门望着,就这么望着,一直望着。大红喉头滚动,双手死死攥着,她想喊妈,这20年亏欠的称呼。她就这么生生地望着,像想把丢掉的时间都看回来,死死咬着的后牙带着刻骨的恨意,满脸的委屈,哭得像一个孩子。能在妈妈眼前委屈的哭一场,是大红这委屈生活的期望。
大红告诉大姨,被拐后的她在被日夜虐打后,只得闭上眼睛认命屈辱地活下去。但我们永远无法想象无耻愚昧的恶是怎样的。
“前面生了两个孩子,生下来性别都不知道就被抱走了,他家卖了钱一部分还了拐我的债,另一部分拿去赌了。”
“隔了两年,接着又生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天杀的不做人的畜生,害我一辈子。”
“他家怕我跑了,几个人压着我去一个熟人诊所那里,把我生孩子的器官割掉了。我不如个畜生,真的畜生不如。”
“他家不打我了,孩子都大了,也打不动了。就是想家,想妈,想哥,我对不起爸,我真的想家了。”
“我回家呆几天就回去,我还有两个孩子不能让他们没妈。”
大红平静地述说着自己20年的生活,字字都是屈辱和苦楚。大姨她说不出话了,光是听就哑了,被剥夺了空气,胸腔剧烈起伏。之后仿佛又被自己劝服了,这是她的命和运,这么一来她对自己的遭遇又和解了。而大红离开了不属于她的家回到了想逃离的家,她的生活充满悲凉和残酷。
3
大姨的大儿子大平,年轻时远走福建务工,不久就做了上门女婿,做了伐木的营生。离家二十几年,每年大姨10月过生日,都会打一个电话,从未变过。
但某年3月,一个电话打来,大平出事了。在伐木锯大树时,因为角度评估有误,那个三人抱粗的大树轰然倒塌,结结实实地压在大平身上。当时就血肉模糊,气息全无。只留下一个11岁大、智力有些迟钝的儿子。大姨白发人送黑发人,感觉天都塌了。
后来,不懂事的我问她想不想大平。大姨只告诉我,他活着也就一年见不了面,也就是少了一个电话的事情,只当没有见过他。
回到家,我就再没见过大姨掉一滴泪。或许我的记忆里她就不曾落泪。往后她信了佛。不得不说她找到了生活残酷真相自洽的途径。她的佛告诉她,命里就缺子女缘。生活里的苦楚以信仰为桥梁的方式架在真实生活中,没那么难以承受,只要再一次认命。
4
2020年初疫情暴发期间,大姨已经离婚的那个男人在五楼的自家窗边失足跌落,来不及送医就停了心跳没了呼吸。据说邻居们在事发当时听见了争吵,和新一任的女友,喝了酒的男人高声谩骂,污言秽语不绝于耳。
这个前夫曾经在每一次酒后对大姨施暴,打倒大姨并骑上她的身体,抡着拳头砸,直到体力耗尽昏昏欲睡,仿佛只有这样喝酒的乐趣才真正结束。
我曾听长辈背后嘀嘀咕咕:“谁知道是自己掉的还是别人推得,做人果真不能太过了。”
疫情当下,医疗经力吃紧,家属认同,邻里没有异议,以失足告终。就这样,暴力欺压大姨十几年的人彻彻底底的消失于人世间。我的大姨就这样倥偬一人迎接往后的岁月。
日子轻轻巧巧的溜走了,但大姨的生活像是溪水归河,有一种自然而然的节奏,自有自的归属感。
小慧在区里花店打工,时常带着男友回老家钓鱼在我家吃饭。每次打电话给大姨要回家,大姨都是买菜做饭去路口等着她。
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记得,这世界上有这样一个人,吃苦耐劳,乐天顽强。但我知道,我会记得,我们来来往往于这世间,一切都终将会消散。唯有记忆是一种馈赠,让我始终望着来时的路。
我们或许时常为生活的平凡和寡淡而气馁,但我相信没有人想要悲苦交加风雨一生的故事。每当我想到大姨的经历,我对她肃然起敬,她真的有努力地给自己的人生一个交代。这样的乐天知命的基因,我希望在没有曲折的经历下的我们也能拥有。永远爱着活着这件事情。
本栏目长期接受热点事件当事人、人生经历、职业故事等主题故事投稿。一经采用,将获得丰厚稿酬。投稿发送至wangyihaogushi@163.com
移动支付宝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