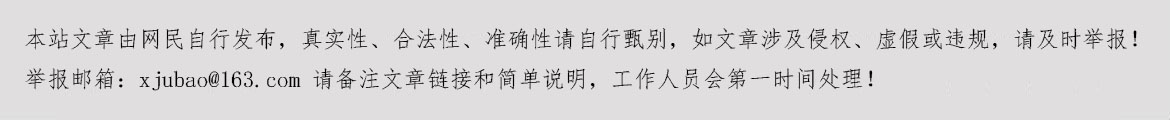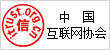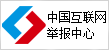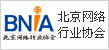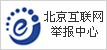1973,杨星火把乃堆拉官兵,比作是西藏高原上的“雪域雄鹰”
2021-10-20 22:11:03
工作笔记31杨星火
乃堆拉哨所的红旗飘扬
一、采访157团2营5连副指导员陈克福
我是1970年8月初来到二营五连驻地乃堆拉。乃堆拉,藏语译为“风雪最大的地方”。乃堆拉位于亚东西南方向29公里处,亚东公路直通乃堆拉山口,山口顶部海拔4400—4600米左右,两侧地形陡峻。边境线长二千余米,共分若干个执勤点。这里风雪大雾四季不断,每年平均有4个月大雪封山,有时达半年以上,大雾笼罩长达200多天。海拔4300多米的乃堆拉哨所与印军哨所阵地仅一网之隔。
印方由18个阵地编成,约一个加強营兵力;公路也通至山口。双方公路只有30米左右未接通。正面30米处,有印一个观察所。
印军驻山口的哨所居高临下,地形对我不利。乃堆拉山口是中锡边界主要山口之一,也是双方兵力对峙之地。与印军一线相隔,尺咫对峙。距敌阵地最近点30米。我们既要同武装敌人作斗争,又要同金钱美女作斗争,还要同恶劣的气候作斗争,政策性强,策略性高。
乃堆拉哨所的一号阵地
(一)阶级教育。
划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荣与耻界限;苦与乐的界限;生与死的界限。敢同恶魔争高下,不向印度反动派让一寸土地。一排三班守一号阵地,比全连阵地高100多米。全班同志却说:“我们每站一班岗,都是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我们守卫的边防是中国领土,决不能守丢一寸。”班长陸世龙﹙上海人﹚,他带头用麻袋背石头修工事,维修堑壕,每一麻袋石头在80到110斤左右。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战士们都自觉跟着班长干。该班的堑壕任何时候都保持着战备的要求,抗敌的要求。他们把艰苦环境当成磨练红心的好地方。吃苦不叫苦,再累也不怕累。
六0炮班把仇恨集中在炮弹上,风雪中坚持演练,他们的口号是:“为保卫毛主席吃苦最幸福,为消灭入侵敌人献身最光荣!”
守卫乃堆拉哨所的制高点
(二)政策教育
我们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中钖边境政策规定》、《阵地管理具体规定》,“五不”规定,即:不吃亏、不示弱、不主动惹事、不开第一枪、不越界一步。上级还规定不得丢失任何东西。熟悉国界和边境的一草一木一石。
1970年10月3日,三号阵地上,机枪三班许开成見对方阵地上寂静,甩石头试探。次日就开始有动静。
每月评论党员,办好教育学习班,分析内部思想情况,防止出政治事故。扫阵地,修补工事,雪再大,交通壕也要保持畅通。白天昼夜背水,利用雾天搞好战备训练。
铲雪开路
藏族战士平措,1970年入伍,团员,荣立三等功一次。他向申忠扬说:“哥哥是名党员,我是吃苦的农奴,不能越境私跑。我家过去被农奴主剥削,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非人生活。现在在国界上站岗执勤,一定要珍惜家庭荣誉,自己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一定要珍惜”。他说:“印度兵瞎宣传印度有自由,我们就批判。他那个种姓社会制度,人民有自由吗?我们在旧社会有自由吗?”
一班长,1969年入伍,经常对全班同志进行“五不准”和一规定、《阵地管理具体规定十条》的教育。厕所相距住地约三十米,每个战士“上厕所”时都得“招呼”一声,大家都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有时凉晒衣、帽、鞋、袜、床单、枕巾、被褥等物品必须用夹子、绳索固定牢实,以免被风刮到国外去了。有次刮大风,将放在工亊顶上的一小片牛毛毡吹到边境线上,我们马上组织人员去捡回来。收到家信看后就烧掉了,怕引起涉外亊件。报刊杂志更有严格管理规定。我们每个战士主动严格执行边防政策,大事小事,言谈举止做到有理有节有利,在边防上打好主动仗。
一班长带领班里的同志坚守在二号阵地,坚持做好全班思想政治工作,全班人员思想稳定。每个同志能正确对待家里的困难,他们说:“不来当兵,家里有时同样会有困难,父母同样会患病,这是人类自然规律,不可逾越”。
八班全班战士住守在三号坑道,石洞子还未遮住,毛石洞,四面凹凸不平,走路一不小心,就会踢伤脚趾甲。冬天洞壁洞顶,吊起冰珠成林,雪白好看;地面结冰一尺多厚,走起路来,鞋底发出嗞嗞的响声。夏天外面下大雨,洞内顶上石缝下小雨,床上用洗脸盆子接水,狗皮褥子都潮湿,霉味熏鼻难闻。冬天到湖边去背水,来回两小时;下雪天就用雪化水饮用。异常艰苦,室内常年滴水,也就是乃堆拉流传的“夏住水帘洞,冬住水晶宮”。
八班长利用两种制度、两种军队的事实来教育战士。对面士兵每顿一张面饼,长官经常打士兵,士兵只有嚎声啼哭;有时扯胡子,痛得泪水直流,冬天穿得也那么单薄。这是大家都能看得见的事实。我军官兵在生活上都是一致的,每天生活费都是1元2角8分钱;政治上是平等的,沒有听说我军干部打骂战士的,谁也不敢打谁;衣着都是一样,干部服装多两个篼。这些都可以作自我对比,这些都是两种军队制度不同的体现。
印军周六有时故意弄些女人到山口上来,满脸涂脂抹粉,身上穿得花花绿绿的,怪模怪样的,走起路来妖里妖气的;还怪声怪调的说:“你们何苦远离家乡妻子儿女来这高山老林受苦受累”。我们的战士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为革命吃苦,保边疆,打豺狼”;有一次,有个战士对她们说:“你们每周周末上山口来帮助印军作宣传,为他们“慰问服务”,你们又何苦呢?我们也理解你们是生活所逼,没有办法才来的,快回家去吧。
全连同志认识到,我们与印军面对面站岗,国际形势一有风云变幻,印军就有风吹草动。为此,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提高政治觉悟,永远跟党走,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要守好阵地,守好国门,让祖国和人民放心。
二、采访朱家友(炮班班长)
我家里解放以前很穷,没有吃的,父亲去摘榆树叶,不小心把树枝碰断了,被地主毒打一顿。外出讨饭,身上被地主的狗咬伤多处,至今留下伤疤。母亲来到我家,一床被子都没有盖的,盖麻布片。在解放以前,不仅是我一家才有这样的苦大仇深,中国大地上绝大多数家庭都如此。现在生活好了,有吃有穿,手上戴有手表,有收音机,能听国内国际新闻。
原来有些老同志盼望着退伍,回到天俯之国,回到美丽的家乡。通过批林整风学习后,使全连同志认识到,我们与印军咫尺相望,与他们就一道铁丝网的距离相峙,我们不守好这边防前哨,保卫好红色江山,谁来守卫边疆?老兵们服役三年,树立了“一人吃苦,万人乐”的思想,在乃堆拉山口享受着“三个三”,即:三年没有脱过棉衣,一年四季都穿着,所以称老兵为“老棉裤”;三年没有洗过澡,连喝的水、洗脸水、漱口水都困难,从何谈洗澡呢?三年没有下过山去亚东县一次。有的老兵退伍回去后,对乃堆拉山口自然环境、边境有多少固定石头、我军的工事如何等等,他们终身不忘。叫他们说出亚东县城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就哑口无言,一概不知。尽管如此,战士们也无怨无悔,一颗红心献给乃堆拉山口。
三、采访刘文义(二排副排长)
我1969年入伍,今年(1973年)退伍没有我。我认为是连队领导“吭”了自己,整了我,与我过意不去。我带着怨气去找领导说个一、二、三,准备说个高低。可是连队领导却和蔼可亲的对我说:“你是一名老兵、连队的一名骨干。我们面对凶恶的敌人,连队没有军事较为过硬的骨干,谁来言传身教?谁来带领新同志学习军事技术?谁来增强他们保卫边境的能力?谁来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谁来传承发杨乃堆拉“以哨卡阵地为家”的光荣传统?
经过领导的一席问话,我满腔的怨气,烟消云散了。我深刻认识到:我们乃堆拉军人应把革命利益应放在第一位,服从党的需要,握紧手中钢枪,安心守卫乃堆拉,对面豺狼胆敢来犯,就彻底消灭他。
四、何希万烈士﹙九班战士﹚
何希万入伍以来,学习刻苦,工作踏实,勤劳肯干,憨厚老实,不爱多言多语。因高原气候与自然环境、他在多方面水土不服,经常腹泻拉肚。但他在班上从来不讲不呻吟,坚持站岗执勤,带病工作。有一天砍树,他倒在抬树木的路上。战友们把他送往团卫生队。经医生诊断:他小肠发炎、受损严重,需手术治疗。可他手术后,仍医治无效身故。团里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年轻的战士就这样把自己宝贵的生命奉献在雪域高原。
我们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我们用青春、热血至生命来守护。哪怕狂风暴雪,严寒冰冻,祖国的山河不能丢!
年复一年,一茬茬官兵在这风雪边关,圆满完成戍边任务。乃堆拉哨所不愧是西藏高原上的一只“雪域雄鹰”。
(注:本文插图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杨星火四川省威远县人。1925年生。国立中央大学化工系毕业。1949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随十八军进藏。曾参加修筑川藏公路、平息西藏叛乱和民主改革、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边防建设等。在西藏工作20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军旅诗人。
本文由刘光福、雪松整理。
作者